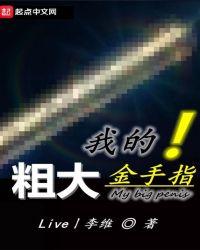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1部分(第1页)
此时文革已过,当年被政治狂热弄得发疯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
当年的整我们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和姐姐讲故事——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整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
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间的事,因此当后来母亲告诉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鲜血,某某人让外公给蒋介石的纸人下跪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怎么可以和颜悦色地来我们家串门,哄小孩子开心呢?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
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邻村任庄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村民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人挂彩,好在没死人。
当年整我们家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
外婆把我领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又心疼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时记忆中村子里的疯子多。
一千多人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疯子。
有文革时不堪虐待疯的,有文革后失势疯的,也有因为自责疯的。
和我们家在一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舅”
,由于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鼓励下把自己的父亲踹得口吐鲜血而自责不已,不久就疯了。
他总是浑身上下别满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语。
当时,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
每天晚上下工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分,有时争吵,有时嬉闹,感觉非常民主。
生产队的会计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年轻人,也是五服以内的亲戚,我们都叫他旦妞哥。
旦妞哥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气,当时二十出头,刚刚高中毕业,在队里算是个文化人。
外公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但因为干活卖力,总是被评上十二个或者是十四个工分(「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分采取十分制,一个标准棒劳力的得分是十分)。
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卖馒头晚上回家时,被汽车撞死了。
后来那辆肇事汽车逃逸,家里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尸体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几天才被领走。
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是难过了一些日子。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本来就非出自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意愿,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松,农民就为“私”
字忙碌起来。
当时,我和常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每天早上上工时,队长就拿个破铁块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
,于是社员们就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来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上五分钟休息半小时。
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
我和姐姐是外来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诸如拾马粪、拔杂草之类的轻活干,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
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时见到草丛里有一条蛇,吓得我发了好几天烧,把外婆心疼坏了。
文革结束以后,以往被禁绝的农村戏班子又活跃起来,我常随外公去公社看戏。
当时公社有一个礼堂,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座位”
都是砖头垒成的墩子。
那时刚刚恢复这些东西,因此每次看戏时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戏都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
我记住了几次看戏的内容,有《穆桂英挂帅》、《寇准背靴》、《空城计》、《打金枝》等等。
有些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可外公却是百看不厌,有时还步行十几里路,到更远的公社、集镇去看。
戏院门口卖小吃的、卖西瓜、卖花生瓜子的一个挨着一个,当时一块西瓜卖一毛钱。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除了过年,就是赶集了。
当时离我们那个村子六里路开外,有一个叫袁公店的集镇,是外婆的娘家,比较大,每年有一个大集。
文革期间这个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
割掉了,此时刚刚恢复,因此盛况空前。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奇洛李维斯回信清明谷雨
- 服软向雾
- 已读不回微风几许
- 我修合欢后他们都疯了公子永安
- 钟离先生一直在穿越也河
- 洪荒:开局给女娲剧透第二眠
- 反派:师尊师姐求你们了天行见道
- 妹控(兄妹,H)莉莉香
- 蜜汁樱桃( 校园 )苦咖啡
- 无敌从我看见BOSS血条开始我也很绝望
- 今天也没能扬帆起航春风遥
- 秘闻(公媳)向雾
- 留守乡村的少年曾呓
- 逆袭死亡航线[重生]时玖远
- 淼淼(父女)谁又偷猫肉
- 轮回塔爱哭的小十七
- 官运:青云之路张正廷刘浮生
- 别叫我邪神水果中的瞳神
- 二哈和他的白猫师尊肉包不吃肉
- 石小小的快乐生活(高辣、、等)kfbjk
- 聊骚(公媳出轨)凉凉
- 周轻羽赵烟芸我特别白不灭神主
- 我行让我上[电竞]酱子贝
- 纳妾+番外南胡唐
- 欲言难止麦香鸡呢
- 蜜汁樱桃( 校园 )苦咖啡
- 开局奖励双修功法,女帝说想躺平三最
- (主奴调教)被哥布林俘获的最强女骑士最讨厌涩涩了
- 末日:我能自选异能强点正常吧星梦辰缘
- 聊骚(公媳出轨)凉凉
- 你居然想睡我(1v2)刘千万
- 轮回塔爱哭的小十七
- 优质肉棒攻略系统(高辣文)寀小花
- 欲言难止麦香鸡呢
- 今天也没能扬帆起航春风遥
- 重生之毒妃梅果
- 我修合欢后他们都疯了公子永安
- 淫荡幼女一条狗
- 当我穿成历史名人的宠物置业
- 石小小的快乐生活(高辣、、等)kfbjk
- 差错【兄妹H】一包熏咸鱼
- 肉文女配不容易[快穿H]纪双禾
- 于青花卷
- 幼女天空下_山村老师 作者:万恶我为首击水三千
- 玄幻:勾栏听曲的我,模拟成神第二十五时
- 呦呦爱吃肉(乱伦 np)奶味大肉棒
- 综艺:儿子对比,全网父母酸了!半刻花生
- 【百合gl】纯gl短篇合集夜来风雨声
- 天官赐福 完结+番外墨香铜臭
- 我只喜欢你的人设[娱乐圈]稚楚
- 全骑士之力的我怎么会穿越到混沌闪光嘿嘿
- 卧底?三年又三年我成了魔道掌教一天十更
- 谍影:命令与征服拉丁海十三郎
- 重生在电影的世界盏茶煮酒
- 两界穿梭:奋斗在1970九毛九
- 坏蛋之风云再起2宅阿男
- 全民游戏:从丧尸末日开始挂机帝国黑铁战士
- 这就是牌佬的世界吗?亚达贼!灰宅
- 木叶:我,忍战樱,全靠技术!许青鸾
- 最强修仙法星辰衍变游戏渣男
- 快穿诡异迷途的小正
- 相错亲结对婚,腹黑老公太撩人胡杨三世
- 从超兽武装开始盘点云朵山药片
- 别叫我邪神水果中的瞳神
- 魂穿修真界:我的空间能藏娇天辰星语
- 从海贼开始横推万界燕云因陀罗
- 斗罗:穿成千仞雪跟班,被迫成神沈亦初
- 当众休夫后,摄政王十里红妆高调求娶红小果
- 美漫:开局指导蝙蝠侠遇牧烧绳
- 觉醒的作精女配被虐文女主抱走了清圆一一
- 一人之下:一人往矣英雄骑士
- 五灵根翊男天
- 异世界宗教胜利居然如此简单?大斗猫
- 从武大郎开始的快穿之旅琰琰睡不着
- 斗罗:从武魂时之虫开始棋解 pan>
- 慎言别雀
- 旦那(父女 1v1)春与愁几许
- 炙豹煮鹤紫雨天辰
- 我的竹马他离家出走了石头星
- 答应青梅女友婚后初夜,我却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被痴女们不断榨精调酒师
- 你好,路知南不是妖腻
- 母子乱伦图鉴南宫大官人
- 热雨李诶诶
- 城里的美女教师怎会成为村中少年的胯下母狗?支教教师的淫堕之旅...波奇的音静二号机
- 既然爆发丧尸末日了那一定要好好和可怜又可爱的女丧尸们做爱吧天野伊吹
- 病变百骸
- 浪与礁石liy离
- 深情渣男石头星
- 不逢春酒猫儿
- 傍晚降雨林林安